中国大运河,是世界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运河,被国际上称为“最具影响力的水道”。它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,更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,曾经对中国经济、文化产生巨大影响,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大运河,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大地上,滋养着中原文化、燕赵文化、齐鲁文化、江淮文化、吴越文化,沿岸城镇因水而建,因水而兴,形成独特的运河文化带。这里自古是中国的“财赋之地,人文渊薮”。
在漫长的岁月中,在这条河道里,行走着各色人等,上自帝王,下至官员;有应试举子,也有商贾巨富。他们或舟行水道,或逗留驿馆,或河边送行,记其见闻,发其慨叹,留下了大量的运河诗篇。这些诗作,评述运河开凿的功过,盛赞沿途城镇的风光,咏颂水利闸坝的壮观,描写行进水道的险情,诉说运夫船工的艰辛,抒发送友、思乡、羁旅之情,兼具文学与历史价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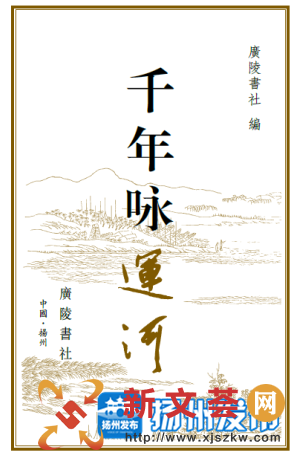
《千年咏运河》精选145位诗人题咏运河的诗词215篇,入选作品的时间自南朝至清末,涉及运河干流、支流沿线,力求全方位反映运河文化风貌。选收作品时,前附作者小传,简介作者生平与诗作风格。诗后有注,对个别生僻字词或与运河有关地名作简要解读。部分作品附录“链接”,侧重介绍运河相关城市、集镇及遗存,有助于世人瞭解运河沿岸的人文风貌。选配历代评点,有利于读者对作品或诗人创作风格的理解与赏析。书中选配部分古代版画,多为运河胜景。宣纸线装,套色精印,让读者在赏鉴中国古典诗词之美的过程中,去领略中国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流淌着千古诗意
留住运河文脉与记忆
大运河是一条流淌着千年诗意的河道。隋开运河,沟通南北。唐人以史为鉴,反思“隋亡”,常以汴河、隋堤为题赋诗,对隋炀帝开凿运河进行评述,褒贬不一。皮日休《汴河怀古》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”,表达了他对隋开运河的肯定。
徐州处于汴、泗、黄、运四河交错之地,泗水在徐州城东北与西来的汴水相会后继续东南流出徐州,其间河道狭窄,形成了史称“徐州三洪”的三处急流。“三洪之险闻于天下”,苏轼《百步洪》“有如兔走鹰隼落,骏马下注千丈坡。断弦离柱箭脱手,飞电过隙珠翻荷”,博喻绘景,描写出船行洪流中的迅疾惊险。
“岸蓼疏红水荇青,茨菰花白小如萍”,杨士奇《发淮安》拈出蓼草花的淡红、荇菜根的碧青、茨菰花的嫩白,盛赞运河水乡如画的美景。
“落日孤舟下石梁,蒹葭寒色起苍茫。青天忽堕大湖水,明月长流万里光。”宗臣的《南旺湖夜泊》再现南旺湖天水一色,月光如练的夜景。而谢肇淛《南旺挑河行》“堤遥遥,河弥弥,分水祠前卒如蚁。鹑衣短发行且僵,尽是六郡良家子。浅水没足泥没骭,五更疾作至夜半……”则道出河工的疾苦和悲惨遭遇。
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,运河一直承担着南粮北运的职能,时称“漕运”。龚自珍南归途经淮浦,亲眼看到成千只粮船沿运河北上的情景。当他深夜听到牵夫们沉重的拉船号子,想到自己也曾食用这些漕米,不禁惭感交并,发出“只筹一缆十夫多,细算千艘渡此河”的慨叹。
王之涣《送别》:“杨柳东风树,青青夹御河。近来攀折苦,应为别离多。”崔颢《晚入汴河》:“昨晚南行楚,今朝北溯河。客愁能几日?乡路渐无多。”韦建《泊舟盱眙》:“平沙依雁宿,候馆听鸡鸣。乡国云霄外,谁堪羁旅情。”一首首诗,催生出诗人送友的离别情、回家途中的还乡情、客寄他乡的羁旅情。
运河淌千年,文脉永续传。

 新闻热线:025–52777966
新闻热线:025–52777966